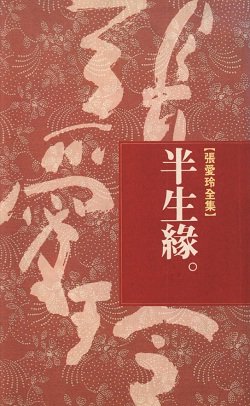房間裏的空氣冷冰冰的,她開口說話,就像是赤著腳踏到冷水裏去似的。然而她還是得說下去。她顫聲道:﹁你不知道,我這兩年的日子都不是人過的。鴻才成天的在外頭鬼混,要不是因為有這孩子,他早不要我了。你想等我死了,這孩子指不定落在一個什麼女人手裏呢。所以我求求你,你還是回去吧。﹂曼楨道:﹁這些廢話你可以不必再說了。﹂曼璐又道:﹁我講你不信,其實是真的;鴻才他就佩服你,他對你真是同別的女人兩樣,你要是管他一定管得好的。﹂曼楨怒道:﹁祝鴻才是我什麼人,我憑什麼要管他?﹂曼璐道:﹁那麼不去說他了,就看這孩子可憐,我要是死了他該多苦,孩子總是你養的。﹂
曼楨怔了一會,道:﹁我趕明兒想法子把他領出來。﹂曼璐道:﹁那怎麼行,鴻才他哪兒肯哪!你就是告他,他也要傾家蕩產跟你打官司的,好容易有這麼個寶貝兒子,哪裏肯放手。﹂曼楨道:﹁我也想著是難。﹂曼璐道:﹁是呀,要不然我也不來找你了。只有這一個辦法,我死了你可以跟他結婚︱︱﹂曼楨道:﹁這種話你就不要去說它了。我死也不會嫁給祝鴻才的。﹂曼璐卻掙扎著把孩子抱了起來,送到曼楨跟前,嘆息著道:﹁為來為去還不是為了他嗎。你的心就這樣狠!﹂
曼楨實在不想抱那孩子,因為她不願意在曼璐面前掉眼淚。但是曼璐只管氣喘喘地把孩子掗了過來。她還沒伸手去接,孩子卻哇的一聲哭了起來,別過頭去叫著﹁媽!媽!﹂向曼璐懷中躲去。他當然只認得曼璐是他的母親,但是曼楨當時忽然變得無可理喻起來,她看見孩子那樣子,覺得非常刺激。
曼璐因為孩子對她這樣依戀,她也悲從中來,哽咽著向曼楨說道:﹁我這時候死了,別的沒什麼丟不下的,就是不放心他。我真捨不得。﹂說到這裏,不由得淚如泉湧。曼楨心裏也不見得比她好過,後來看見她越哭越厲害,而且喘成一團,曼楨實在不能忍受了,只得硬起心腸,厭煩地皺著眉說道:﹁你看你這樣子!還不趕快回去吧!﹂說著,立刻掉轉身來跑下樓去,把汽車上的阿寶和張媽叫出來,叫她們來攙曼璐下樓。曼璐就這樣哭哭啼啼的走了,奶媽抱著孩子跟在她後面。
曼楨一個人在房間裏,她把床上亂堆著的被窩疊疊好,然後就在床沿上坐下了,發了一會呆。根本一提起鴻才她就是一肚子火,她對他除了仇恨還有一種本能的憎惡,所以剛才不加考慮地就拒絕了她姊姊的要求。現在冷靜下來仔細想想,她這樣做也是對的。她並不是不疼孩子,現在她除了這孩子,在這世界上再也沒有第二個親人了。如果能夠把他領出來由她撫養,雖然一個未婚的母親在這社會上是被歧視的,但是她什麼都不怕。為他怎麼樣犧牲都行,就是不能夠嫁給鴻才。
她不打算在這裏再住下去了,因為怕曼璐會再來和她糾纏,或者又要叫她母親來找她。她向學校提出辭職,但是因為放寒假前已經接受了下學期的聘書,所以費了許多唇舌才辭掉了,另外在別處找了個事做會計。她從前學過會計的。找到事又找房子,分租了人家一間房間,二房東姓郭。有一天她下了班回去,走到郭家後門口,裏面剛巧走出一個年輕女子,小圓臉兒,黃黑皮色,腮頰上的胭脂抹得紅紅的,兩邊的鬢髮吊得高高的,穿著一件白地子紅黃小花麻紗旗袍。原來是阿寶。︱︱怎麼會又被他們找到這裏來了?曼楨不覺怔了一怔。阿寶看見她也似乎非常詫異,叫了聲﹁咦,二小姐!﹂阿寶身後還跟著一個男子,曼楨認得他是荐頭店的人,這才想起來,郭家的一個老媽子回鄉下去了,前兩天他們家從荐頭店裏叫了一個女傭來試工,大概不合適,所以又另外找人。看樣子阿寶是到郭家來上工的,並不是奉命來找曼楨的,但是曼楨仍舊懶得理她,因為看見她不免就想起從前在祝家被禁閉的時候,她也是一個幫兇。固然她們做傭人的人也是沒辦法,吃人家的飯,就得聽人家指揮,所以也不能十分怪她,但無論如何,曼楨看到她總覺得非常不愉快,只略微把頭點了一點,腳步始終沒有停下來,就繼續地往裏面走。阿寶卻趕上來叫道:﹁二小姐大概不知道吧,大小姐不在了呀。﹂這消息該不是怎樣意外的,然而曼楨還是吃了一驚,說:﹁哦?是幾時不在的?﹂阿寶道:﹁喏,就是那次到您學校裏去,後來不到半個月呀。﹂說著,竟眼圈一紅,落下兩點眼淚。她倒哭了,曼楨只是怔怔地朝她看著,心裏覺得空空洞洞的。
阿寶用一隻指頭頂著手帕,很小心地在眼角擦了擦,便向荐頭店的人說:﹁你可要先回去?我還要跟老東家說兩句話。﹂曼楨卻不想跟她多談,便道:﹁你有事你還是去吧,不要耽擱了你的事。﹂阿寶也覺得曼楨對她非常冷淡,想來總是為了從前那枚戒指的事情,便道:﹁二小姐,我知道你一定怪我那時候不給你送信,咳,你都不知道︱︱你曉得後來為什麼不讓我到你房裏來了?﹂她才說到這裏,曼楨便皺著眉攔住她道:﹁這些事還說它幹什麼?﹂阿寶看了看她的臉色,便也默然了,自己抱住自己兩隻胳膊,只管撫摸著。半晌方道:﹁我現在不在他家做了。我都氣死了,二小姐你不知道,大小姐一死,周媽就在姑爺面前說我的壞話,這周媽專門會拍馬屁,才來了幾個月,就把奶媽戳掉了,小少爺就歸她帶著。當著姑爺的面假裝的待小少爺不知多麼好,背後簡直像個晚娘。我真看不過去,我就走了。﹂
她忽然變得這樣正義感起來。曼楨覺得她說的話多少得打點折扣,但是她在祝家被別的傭人擠出來了,這大約是實情。她顯然是很氣憤,好像憋著一肚子話沒處說似的,曼楨不邀她進去,她站在後門口就滔滔不絕地長談起來。又說:﹁姑爺這一向做生意淨蝕本,所以脾氣更壞了,家當橫是快蝕光了,虹橋路的房子也賣掉了,現在他們搬了,就在大安里。說是大小姐有幫夫運,是真的呵,大小姐一死,馬上就倒霉了!他自己橫是也懊悔了,這一向倒霉瞌盹的蹲在家裏,外頭的女人都斷掉了,我常看見他對大小姐的照片淌眼淚。﹂
一說到鴻才,曼楨就露出不耐煩的神氣,彷彿已經在後門口站得太久了。阿寶究竟還知趣,就沒有再往下說,轉過口來問道:﹁二小姐現在住在這兒?﹂曼楨只含糊地應了一聲,就轉問她:﹁你到這兒來是不是來上工的?﹂阿寶笑道:﹁是呀,不過我看他們這兒人又多,工錢也不大,我不想做。我託託二小姐好吧,二小姐有什麼朋友要用人,就來喊我,我就在對過的荐頭店裏。﹂曼楨也隨口答應著。
隨即有一剎那的沉默。曼楨很希望她再多說一點關於那孩子的事情,說他長得有多高了,怎樣頑皮︱︱一個孩子可以製造出許多﹁軼聞﹂和﹁佳話﹂,為女傭們所樂道的。曼楨也很想知道,他說話是什麼地方的口音?他身體還結實嗎?脾氣好不好?阿寶不說,曼楨卻也不願意問她,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羞於啟齒。
阿寶笑道:﹁那我走了,二小姐。﹂她走了,曼楨也就進去了。
阿寶說祝家現在住在大安里,曼楨常常走過那裏的,她每天乘電車,從她家裏走到電車站有不少路,這大安里就是必經之地,現在她走到這裏總是換到馬路對過走著,很擔心也許會碰見鴻才,雖然不怕他糾纏不清,究竟討厭。
這一天,她下班回來,有兩個放學回來的小學生走在她前面。她近來看見任何小孩就要猜測他們的年齡,同時計算著自己的孩子的歲數,想著那孩子是不是也有這樣高了。這兩個小孩當然比她的孩子大好些,總有七八歲的光景,一律在棉袍上罩著新藍布罩袍,穿得胖墩墩的。兩人像操兵似的並排走著,齊齊地舉起手裏的算盤,有節奏地一舉一舉,使那算盤珠發出﹁批!批!﹂的巨響,作為助威的軍樂。有時候又把算盤扛在肩上代表槍枝。
曼楨在他們後面,偶爾聽見他們談話的片段,他們的談話卻是太沒有志氣了,一個孩子說:﹁馬正林的爸爸開麵包店的,馬正林天天有麵包吃。﹂言下不勝艷羨的樣子。
他們忽然穿過馬路,向大安里裏面走去。曼楨不禁震了一震,雖然也知道這決不是她的小孩,而且這一個衖堂裏面的孩子也多得很,但是她不由自主地就跟在他們後面過了馬路,走進這衖堂。她的腳步究竟有些遲疑,所以等她走進去,那兩個孩子早已失蹤了。
那是春二三月天氣,一個凝冷的灰色的下午。春天常常是這樣的,還沒有嗅到春的氣息,先覺得一切東西都發出氣味來,人身上除了冷颼颼之外又有點癢梭梭的,覺得骯髒。雖然沒下雨,衖堂裏地下也是濕黏黏的。走進去,兩旁都是石庫門房子,正中停著個臭豆腐乾擔子,挑擔子的人叉著腰站在稍遠的地方,拖長了聲音吆喝著。有一個小女孩在那擔子上買了一串臭豆腐乾,自己動手在那裏抹辣醬。好像是鴻才前妻的女兒招弟。曼楨也沒來得及向她細看,眼光就被她身旁的一個男孩子吸引了去,一個四五歲的男孩子,和招弟分明是姊弟,兩人穿著同樣的紫花布棉袍,雖然已經是春天了,他們腳上還穿著老棉鞋,可是光著腳沒穿襪子,那紅赤赤的腳踝襯著那舊黑布棉鞋,看上去使人有一種奇異的淒慘的感覺。那男孩子頭髮長長的,一直覆到眉心上,臉上雖然髒,彷彿很俊秀似的。
曼楨心慌意亂地也沒有來得及細看,卻又把眼光回到招弟身上,想仔細認一認她到底是不是招弟。雖然只見過一面,而且是在好幾年前,曼楨倒記得很清楚。照理一個小孩是改變得最快的,這面黃肌瘦的小姑娘卻始終是那副模樣,甚至於一點也沒長高︱︱其實當然不是沒有長高,她的太短的袍子就是一個證據。
那招弟站在豆腐乾擔子旁邊,從小瓦罐裏挑出辣醬抹在臭豆腐乾上。大概因為辣醬是不要錢的,所以大量地抹上去,就像在麵包上塗果子醬似的,把整塊的豆腐乾塗得鮮紅。挑擔子的人看了她一眼,彷彿想說話了,結果也沒說。招弟一共買了三塊,穿在一根稻草上,拎在手裏吃著。她弟弟也想吃,他踮著腳,兩隻手撲在她身上,仰著臉咬了一口。曼楨心裏想這一口吃下去,一定辣得眼淚出,喉嚨也要燙壞了。她不覺替他捏一把汗,誰知他竟面不改色地吞了下去,而且吃了還要吃,依舊踮著腳尖把嘴湊上去。招弟也很友愛似的,自己咬一口,又讓他咬一口。曼楨看著她那孩子的傻相,不由得要笑,但是一面笑著,眼眶裏的淚水已經滴下來了。
她急忙別過身去,轉了個彎走到支弄裏去,一面走一面抬起手背來擦眼淚。忽然聽見背後一陣腳步聲,一回頭,卻是招弟,向這邊啪噠啪噠追了過來,她那棉鞋越穿越大,踏在那潮濕的水門汀上,一吸一吸,發出唧唧的響聲。曼楨想道:﹁糟了,她一定是認識我。我還以為她那時候小,只看見過我一回,一定不記得了。﹂曼楨只得扭過頭去假裝尋找門牌,一路走過去,從眼角裏看看那招弟,招弟卻在一家人家的門首站定了,這家人家想必新近做過佛事,門框上貼的黃紙條子剛撕掉一半,現在又在天井裏焚化紙錢,火光熊熊。招弟一面看著他們燒錫箔,一面吃她的臭豆腐乾,似乎對曼楨並不注意。曼楨方才放下心來,便從容地往回走,走了出去。
那男孩身邊現在多了一個女傭,那女傭約有四十來歲年紀,一臉橫肉,兩隻蝌蚪式的烏黑的小眼睛,她端了一隻長凳坐在後門口摘菜,曼楨心裏想這一定就是阿寶所說的那個周媽,招弟就是看見她出來了,所以逃到支弄裏去,大概要躲在那裏把豆腐乾吃完了再回來。
曼楨緩緩地從他們面前走過。那孩子看見她,也不知道是喜歡她的臉還是喜歡她的衣裳,他忽然喊了一聲﹁阿姨!﹂曼楨回過頭來向他笑一笑,他竟﹁阿姨!阿姨!﹂地一連串喊下去了。那女傭便嘟囔了一句:﹁叫你喊的時候倒不喊,不叫你喊的時候倒喊個不停!﹂
曼楨走出那個衖堂,一連走過十幾家店面,一顆心還是突突地跳著。走過一家店舖的櫥窗,她向櫥窗裏的影子微笑。倒看不出來,她有什麼地方使一個小孩一看見她就對她發生好感,﹁阿姨!阿姨!﹂地喊著。她耳邊一直聽見那孩子的聲音。她又仔細回想他的面貌,上次她姊姊把他帶來給她看,那時候他還不會走路吧,滿床爬著,像一個可愛的小動物,現在卻已經是一個有個性的﹁人物﹂了。
這次總算運氣,一走進去就看見了他。以後可不能再去了。多看見了也無益,徒然傷心罷了。倒是她母親那裏,她想著她姊姊現在死了,鴻才也未見得有這個閒錢津貼她母親,曼楨便匯了一筆錢去,但是沒有寫她自己的地址,因為她仍舊不願意她母親來找她。
轉瞬已經到了夏天,她母親上次說大弟弟今年夏天畢業,他畢了業就可以出去掙錢了,但是,曼楨總覺得他剛出去做事,要他獨力支持這樣一份人家,那是絕對不可能的。她又給他們寄了一筆錢去。她把她這兩年的一些積蓄陸續都貼給他們了。
這一天天氣非常悶熱,傍晚忽然下起大雨來,二房東的女傭奔到曬台上去搶救她晾出去的衣裳。樓底下有人撳鈴,撳了半天沒有人開門,曼楨只得跑下樓去,一開門,見是一個陌生的少婦。那少婦有點侷促地向曼楨微笑道:﹁我借打一個電話,便當嗎?我就住在九號裏,就在對過。﹂
外面嘩嘩地下著雨,曼楨便請她進來等著,笑道:﹁我去喊郭太太。﹂喊了幾聲沒人應,那女傭抱著一卷衣裳下樓來說:﹁太太不在家。﹂曼楨只得把那少婦領到穿堂裏,裝著電話的地方。那少婦先拿起電話簿子來查號碼,曼楨替她把電燈開了,在燈光下看見那少婦雖然披著斗篷式的雨衣,依舊可以看出她是懷著孕的。她的頭髮是直的,養得長長的擄在耳後,看上去不像一個上海女人,然而也沒有小城市的氣息,相貌很娟秀,稍有點扁平的鵝蛋臉。她費了很多的時候查電話簿,似乎有些抱歉,不時地抬起頭來向曼楨微笑著,搭訕著問曼楨貴姓,說她自己姓張。又問曼楨是什麼地方人,曼楨說是安徽人。她卻立刻注意起來,笑道:﹁顧小姐是安徽人?安徽什麼地方?﹂曼楨道:﹁六安。﹂那少婦笑道:﹁咦,我新近剛從六安來的。﹂曼楨笑道:﹁張太太也是六安人嗎?倒沒有六安口音。﹂那少婦道:﹁我是上海人呀,我一直就住在這兒。是我們張先生他是六安人。﹂曼楨忖了一忖,便道:﹁哦。六安有一個張豫瑾醫生,不知道張太太可認識嗎?﹂那少婦略頓了一頓,方才低聲笑道:﹁他就叫豫瑾。﹂曼楨笑道:﹁那真巧極了,我們是親戚呀。﹂那少婦喲了一聲,笑道:﹁那真巧,豫瑾這回也來了,顧小姐幾時到我們那兒玩去,我現在住在我母親家。﹂
她撥了號碼,曼楨就走開了,到後面去轉了一轉,等她的電話打完了,再回到這裏來送她出去。本來要留她坐一會等雨小些再走,但是她說她還有事,今天有個親戚請他們吃飯,剛才她就為這個事打電話找豫瑾,叫他直接到館子裏去。
她走後,曼楨回到樓上她自己的房間裏,聽那雨聲緊一陣慢一陣,不像要停的樣子。她心裏想豫瑾要是知道她住在這裏,過兩天他一定會來看她的。她倒有點怕看見他,因為一看見他就要想起別後這幾年來她的經歷,那噩夢似的一段時間,和她過去的二十來年的生活完全不發生連繫,和豫瑾所認識的她也毫不相干。她非常需要把這些事情痛痛快快地和他說一說,要不然,那好像是永遠隱藏在她心底裏的一個恐怖的世界。
這樣想著的時候,立刻往事如潮,她知道今天晚上一定要睡不著覺了。那天天氣又熱,下著雨又沒法開窗子,她躺在床上,不停地搧著扇子,反而搧出一身汗來。已經快十點鐘了,忽然聽見門鈴響,睡在廚房裏的女傭睡得糊裏糊塗的,甕聲甕氣地問:﹁誰呀?……啊?……啊?找誰?﹂曼楨忽然靈機一動,猜著一定是豫瑾來了。她急忙從床上爬起來,捻開電燈,手忙腳亂地穿上衣裳,便跑下樓去。那女傭因為是晚上,不認識的人不敢輕易放他進來。是豫瑾,穿著雨衣站在後門口,正拿著手帕擦臉,頭髮上亮晶晶地流下水珠來。
他向曼楨點頭笑道:﹁我剛回來。聽見說你住在這兒。﹂曼楨也不知道為什麼,一看見他,馬上覺得萬種辛酸都湧上心頭,幸而她站的地方是背著燈,人家看不見她眼睛裏的淚光。她立刻別過身去引路上樓,好在她總是走在前面,依舊沒有人看見她的臉。進了房,她又搶著把床上蓋上一幅被單,趁著這背過身去鋪床的時候,終於把眼淚忍回去了。
豫瑾走進房來,四面看看,便道:﹁你怎麼一個人住在這兒?老太太他們都好吧?﹂曼楨只得先含糊地答了一句:﹁她們現在搬到蘇州去住了。﹂豫瑾似乎很詫異,曼楨本來可以趁此就提起她預備告訴他的那些事情,她看見豫瑾這樣熱心,一聽見說她住在這裏,連夜就冒雨來看她,可見他對她的友情是始終如一的,她更加決定了要把一切都告訴他。但是有一種難於出口的話,反而倒是對一個萍水相逢的人可以傾心吐膽地訴說。上次她在醫院裏,把她的身世告訴金芳,就不像現在對豫瑾這樣感覺到難以啟齒。
她便換了個話題,笑道:﹁真巧了,剛巧會碰見你太太。你們幾時到上海來的?﹂豫瑾道:﹁我們來了也沒有幾天。是因為她需要開刀,我們那邊的醫院沒有好的設備,所以到上海來的。﹂曼楨也沒有細問他太太需要開刀的原因,猜著總是因為生產的緣故,大概預先知道要難產。豫瑾又道:﹁她明天就要住到醫院裏去了,現在這兒是她母親家裏。﹂
他坐下來,身上的雨衣濕淋淋的,也沒有脫下來。當然他是不預備久坐的,因為時間太晚了。曼楨倒了一杯開水擱在他面前,笑道:﹁你們今天有應酬吧?﹂豫瑾笑道:﹁是的,在錦江吃飯,現在剛散,她們回去了,我就直接到這兒來了。﹂豫瑾大概喝了點酒,臉上紅紅的,在室內穿著雨衣,也特別覺得悶熱,他把桌上一張報紙拿起來當扇子搧著。曼楨遞了一把芭蕉扇給他,又把窗子開了半扇。一推開窗戶,就看見對過一排房屋黑沉沉的,差不多全都熄了燈,豫瑾在岳家的人想必都已經睡覺了。豫瑾倘若在這裏耽擱得太久了,他的太太雖然不會多心,太太娘家的人倒說不定要說閒話的。曼楨便想著,以後反正總還要見面的,她想告訴他的那些話還是過天再跟他說吧。但是豫瑾自從踏進她這間房間,就覺得很奇怪,怎麼曼楨現在弄得這樣孑然一身,家裏人搬到內地去住,或許是為了節省開銷,沈世鈞又到哪裏去了呢?怎麼他們到現在還沒有結婚?
豫瑾忍不住問道:﹁沈世鈞還常看見吧?﹂曼楨微笑道:﹁好久不看見了。他好幾年前就回南京去了。﹂豫瑾道:﹁哦?﹂曼楨默然片刻,又說了一聲:﹁後來聽說他結婚了。﹂豫瑾聽了,也覺得無話可說。
在沉默中忽然聽見一陣瑟瑟的響聲,是雨點斜撲進來打在書本上,桌上有幾本書,全打濕了。豫瑾笑道:﹁你這窗子還是不能開。﹂他拿起一本書,掏出手帕把書面的水漬擦乾了。曼楨道:﹁隨它去吧,這上頭有灰,把你的手絹子弄髒了。﹂但是豫瑾仍舊很珍惜地把那些書一本本都擦乾了,因為他想起從前住在曼楨家裏的時候,晚上被隔壁的無線電吵得睡不著覺,她怎樣借書給他看。那時候要不是因為沉世鈞,他們現在的情形也許很兩樣吧?
他急於要打斷自己的思潮,立刻開口說話了,談起他的近況,因道:﹁在這種小地方辦醫院,根本沒有錢可賺,有些設備又是沒法省的,只好少僱兩個人,自己忙一點。我雖然是土生土長的,跟地方上的人也很少來往。蓉珍剛去的時候,這種孤獨的生活她也有點過不慣,覺得悶得慌,後來她就學看護,也在醫院裏幫忙,有了事情做也就不寂寞了。﹂蓉珍想必是他太太的名字。
他自己覺得談得時間夠長了,突然站起身來笑道:﹁走了!﹂曼楨因為時候也是不早了,也就沒有留他。她送他下樓,豫瑾在樓梯上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,問道:﹁上次我在這兒,聽見說你姊姊病了,她現在可好了?﹂曼楨低聲道:﹁她死了。就是不久以前的事。﹂豫瑾惘然道:﹁那次我聽見說是腸結核,是不是就是那毛病?﹂曼楨道:﹁哦,那一次……那一次並沒有那麼嚴重。﹂那次就是她姊姊假裝命在旦夕,做成了圈套陷害她。曼楨頓了一頓,便又淡笑著說道:﹁她死我都沒去︱︱這兩年裏頭發生的事情多了,等你幾時有空講給你聽。﹂豫瑾不由得站住了腳,向她注視了一下,彷彿很願意馬上聽她說出來,但是他看見她臉上突然顯得非常疲乏似的,他也就沒有說什麼,依舊轉身下樓。她一直送到後門口。
她回到樓上來,她房間裏唯一的一張沙發椅,豫瑾剛才坐在這上面的,椅子上有幾塊濕印子,是他雨衣上的水痕染上去的。曼楨望著那水漬發了一會呆,心裏有說不出來的惆悵。
今天這雨是突然之間下起來的,豫瑾出去的時候未見得帶著雨衣,一定是他太太給他把雨衣帶到飯館子裏去的。他們當然是感情非常好,這在豫瑾說話的口吻中也可以聽得出來。
那麼世鈞呢?他的婚後生活是不是也一樣的美滿?許久沒有想起他來了。她自己也以為她的痛苦久已鈍化了。但是那痛苦似乎是她身體裏面唯一的有生命力的東西,永遠是新鮮強烈的,一發作起來就不給她片刻的休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