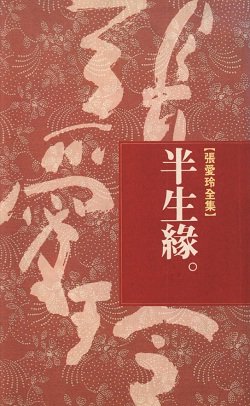她把豫瑾的那杯茶倒在痰盂裏,自己另外倒上一杯。不知道怎麼一來,熱水瓶裏的開水一沖沖出來,全倒在她腳面上,她也木木的,不大覺得,彷彿腳背上被一隻鐵錘打了一下,但是並不痛。
那天晚上的雨一直下到天明才住,曼楨也直到天明才睡著。剛睡了沒有一會,忽然有人推醒了她,好像還是在醫院裏的時候,天一亮,看護就把孩子送來餵奶。她迷迷糊糊地抱著孩子,心中悲喜交集,彷彿那孩子已經是失而復得的了。但是她忽然發現那孩子渾身冰冷︱︱不知道什麼時候死了,都已經僵硬了。她更緊地抱住了他,把他的臉撳沒在她胸前,唯恐被人家發覺這是一個死孩子。然而已經被發覺了。那滿臉橫肉的周媽走過來就把他奪了過去,用蘆席一捲,挾著就走。那死掉的孩子卻在蘆席捲裏掙扎著,叫喊起來:﹁阿姨!阿姨!﹂那孩子越叫越響,曼楨一身冷汗,醒了過來,窗外已是一片雪白的晨光。
曼楨覺得她這夢做得非常奇怪。她不知道她是因為想起過去的事情,想到世鈞,心裏空虛得難過,所以更加渴念著她的孩子,就把一些片段的印象湊成了這樣一個夢。
她再也睡不著了,就起來了。今天她一切都提早,等她走出大門的時候,還不到七點,離她辦公的時間還有兩個鐘頭呢。她在馬路上慢慢地走著,忽然決定要去看看她那孩子。其實,與其說是﹁決定﹂,不如說是她忽然發現了她一直有這意念,所以出來得特別早,恐怕也是為了這個緣故。
快到大安里了。遠遠的看見那衖堂裏走出一行人來,兩個扛夫挑著一個小棺材,後面跟著一個女傭︱︱不就是那周媽嗎!曼楨突然眼前一黑,她身體已經靠在牆上了,兩條腿站都站不住。她極力鎮定著,再向那邊望過去。那周媽一隻手舉著把大芭蕉扇,遮住頭上的陽光,嘴裏一動一動的,大概剛吃過早飯,在那裏吮舐著牙齒。這一幅畫面在曼楨眼中看來,顯得特別清晰,她心裏卻有點迷迷糊糊的。她覺得她又走入噩夢中了。
那棺材在她面前經過。她想走上去向那周媽打聽一聲,死的是什麼人,但是那周媽又不認識她是誰。她這一躊躇之間,他們倒已經去遠了。她一轉念,竟毫不猶豫地走進大安里,她記得祝家是一進門第四家,她逕自去撳鈴,就有一個女傭來開門,這女傭卻是一個舊人,姓張。這張媽見是曼楨,不由得呆了一呆,叫了聲﹁二小姐﹂。曼楨也不和她多說,只道:﹁孩子怎麼樣了?﹂張媽道:﹁今天好些了。﹂︱︱顯然是還活著。曼楨心裏一鬆,陡然腳踏實地了,但是就像電梯降落得太快,反而覺得一陣眩暈。她扶著門框站了一會,便直截地舉步往裏走,說道:﹁他在哪兒?我去看看。﹂那張媽還以為曼楨一定是從別處聽見說孩子病了,所以前來探看,便在前面引路,這是個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,從後門進出的,穿過灶披間,來到客堂裏。客堂間前面一列排門都釘死了,房間裏暗沉沉的,靠裏放著一張大床,孩子就睡在那張床上。曼楨見他臉上通紅,似睡非睡的,伸手在他額上摸了摸,熱得燙手。剛才張媽說他﹁今天好些了,﹂那原來是她們的一種照例的應酬話。曼楨低聲說:﹁請醫生看過沒有?﹂張媽道:﹁請的。醫生講是他姊姊過的,叫兩人不要在一個房間裏。﹂曼楨道:﹁哦,是傳染病。你可知道是什麼病?﹂張媽道:﹁叫什麼猩紅熱。招弟後來看著真難受︱︱可憐,昨天晚上就死了呀。﹂曼楨方才明白過來,剛才她看見的就是招弟的棺材。
她仔細看那孩子臉上,倒沒有紅色的斑點。不過猩紅熱聽說也有時候皮膚上並不現出紅斑。他在床上翻來覆去,不到一分鐘就換一個姿勢,怎樣睡也不舒服。曼楨握住他的手,他的手又乾又熱,更覺得她自己的手冷得像冰一樣。
張媽送茶進來,曼楨道:﹁你可知道,醫生今天還來不來?﹂張媽道:﹁沒聽見說。老爺今天一早就出去了。﹂曼楨聽了,不禁咬了咬牙,她真恨這鴻才,又要霸住孩子不肯放手,又不好好的當心他,她不能讓她這孩子再跟招弟一樣,糊裏糊塗的送掉一條命。她突然站起身來往外走,只匆匆地和張媽說了一聲:﹁我一會兒還要來的。﹂她決定去把豫瑾請來,叫他看看到底是不是猩紅熱。她總有點懷疑祝家請的醫生是否靠得住。
這時候豫瑾大概還沒有出門,時候還早。她跳上一部黃包車,趕回她自己的寓所,走到斜對過那家人家,一撳鈴,豫瑾卻已經在陽台上看見了她,她這裏正在門口問傭人:﹁張醫生可在家?﹂豫瑾已經走了出來,笑著讓她進去。曼楨勉強笑道:﹁我不進去了。你現在可有事?﹂豫瑾見她神色不對,便道:﹁怎麼了?你是不是病了?﹂曼楨道:﹁不是我病了,因為姊姊的小孩病得很厲害,恐怕是猩紅熱,我想請你去看看。﹂豫瑾道:﹁好,我立刻就去。﹂他進去穿上一件上裝,拿了皮包,就和曼楨一同走出來,兩人乘黃包車來到大安里。
豫瑾曾經聽說曼璐嫁得非常好,是她祖母告訴他的,說她怎樣發財,造了房子在虹橋路,想不到他們家現在卻住著這樣湫隘的房屋,他覺得很是意外。他以為他會看見曼璐的丈夫,但是屋主人並沒有出現,只有一個女傭任招待之職。豫瑾一走進客堂就看見曼璐的遺容,配了鏡框迎面掛著。曼楨一直就沒看見,她兩次到這裏來,都是心慌意亂的,全神貫注在孩子身上。
那張大照片大概是曼璐故世前兩年拍的,眼睛斜睨著,一隻手托著腮,手上戴著一隻晶光四射的大鑽戒。豫瑾看到她那種不調和的媚態與老態,只覺得愴然。他不由得想起他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。那次他也許是對她太冷酷了,後來想起來一直耿耿於心。
是她的孩子,他當然也是很關切的。經他診斷,也說是猩紅熱。曼楨說:﹁要不要進醫院?﹂醫生向來主張進醫院的,但是豫瑾看看祝家這樣子,彷彿手頭很拮据,也不能不替他們打算打算,便道:﹁現在醫院也挺貴的,在家裏只要有人好好的看護,也是一樣的。﹂曼楨本來想著,如果進醫院的話,她去照料比較方便些,但是實際上她也出不起這個錢,也不能指望鴻才拿出來。不進醫院也罷。她叫張媽把那一個醫生的藥方找出來給豫瑾看,豫瑾也認為這方子開得很對。
豫瑾走的時候,曼楨一路送他出去,就在弄口的一爿藥房裏配了藥帶回來,順便在藥房裏打了個電話到她做事的地方去,請了半天假。那孩子這時候清醒些了,只管目光灼灼地望著她。她一轉背,他就悄悄地問:﹁張媽,這是什麼人?﹂張媽頓了一頓,笑道:﹁這是啊……是二姨。﹂說時向曼楨偷眼望了望,彷彿不大確定她願意她怎樣回答。曼楨只管搖晃著藥瓶,搖了一會,拿了隻湯匙走過來叫孩子吃藥,道:﹁趕快吃,吃了就好了。﹂又問張媽:﹁他叫什麼名字?﹂張媽道:﹁叫榮寶。這孩子也可憐,太太活著的時候都寶貝得不得了,現在是周媽帶他︱︱﹂說到這裏,便四面張望了一下,方才鬼鬼祟祟地說:﹁周媽沒良心,老爺雖然也疼孩子,到底是男人家,有許多地方他也想不到︱︱那死鬼招弟是常常給她打的,這寶寶她雖然不敢明欺負他,暗地裏也不少吃她的虧。二小姐你不要對別人講呵,她要曉得我跟你說這些話,我這碗飯就吃不成了。阿寶就是因為跟她兩個人鬧翻了,所以給她戳走了。阿寶也不好,太太死了許多東西在她手裏弄得不明不白,周媽一點也沒拿著,所以氣不伏,就在老爺面前說壞話了。﹂
這張媽把他們家那些是是非非全都搬出來告訴曼楨,分明以為曼楨這次到祝家來,還不是跟鴻才言歸於好了,以後她就是這裏的主婦了,趁這時候周媽出去了還沒回來,應當趕緊告她一狀。張媽這種看法使曼楨覺得非常不舒服,祝家的事情她實在不願意過問,但是一時也沒法子表明自己的立場。
後門口忽然有人拍門,不知道可是鴻才回來了。雖然曼楨心裏並不是一點準備也沒有,終究不免有些惴惴不安,這裏到底是他的家。張媽去開門,隨即聽見兩個人在廚房裏嘁嘁喳喳說了幾句,然後就一先一後走進房來。原來是那周媽,把招弟的棺材送到義塚地去葬了,現在回來了。那周媽雖然沒有見過曼楨,大概早就聽說過有她這樣一個人,也知道這榮寶不是他們太太親生的。現在曼楨忽然出現了,周媽不免小心翼翼,﹁二小姐﹂長﹁二小姐﹂短,在旁邊轉來轉去獻慇勤,她那滿臉殺氣上再濃濃堆上滿面笑容,卻有點使人不寒而慄。曼楨對她只是淡淡的,心裏想倒也不能得罪她,她還是可以把一口怨氣發洩在孩子身上。那周媽自己心虛,深恐張媽要在曼楨跟前揭發她的罪行,她一向把那邋遢老太婆欺壓慣了的,現在卻把她當作老前輩似的尊崇起來,趕著她喊﹁張奶奶﹂,拉她到廚房裏去商量著添點什麼菜,款待二小姐。
曼楨卻在那裏提醒自己,她應當走了。揀要緊的事情囑咐張媽兩句,就走吧,寧可下午再來一次。正想著,榮寶卻說話了,問道:﹁姊姊呢?﹂這是他第一次直接和曼楨說話,說的話卻叫她無法答覆。曼楨過了一會方才悄聲說道:﹁姊姊睡著了。你別鬧。﹂
想起招弟的死,便有一陣寒冷襲上她的心頭,一種原始的恐懼使她許願似的對自己說:﹁只要他好了,我永生永世也不離開他了。﹂雖然她明知道這是辦不到的事。榮寶墊的一床蓆子上面破了一個洞,他總是煩躁地用手去挖它,越挖越大。曼楨把他兩隻手都握住了,輕聲道:﹁不要這樣。﹂說著,她眼睛裏卻有一雙淚珠﹁嗒﹂地一聲掉在蓆子上。
忽然聽見鴻才的聲音在後門口說話,一進門就問:﹁醫生可來過了?﹂張媽道:﹁沒來。二小姐來了。﹂鴻才聽了,頓時寂然無語起來。半晌沒有聲息,曼楨知道他已經站在客堂門口,站了半天了。她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,只是臉上的神情變得嚴冷了些。
她不朝他看,但是他終於趔趄著走入她的視線內。他一副潦倒不堪的樣子,看上去似乎臉也沒洗,鬍子也沒剃,瘦削的臉上膩著一層黃黑色的油光,身上穿著一件白裏泛黃的舊綢長衫,戴著一頂白裏泛黃的舊草帽,帽子始終戴在頭上沒有脫下來。他搭訕著走到床前在榮寶額上摸了摸,喃喃地道:﹁今天可好一點?醫生怎麼還不來?﹂曼楨不語。鴻才咳嗽了一聲,又道:﹁二妹,你來了我就放心了。我真著急。這兩年不知怎麼走的這種悖運,晦氣事情全給我碰到了。招弟害病,沒當它樁事情,等曉得不好,趕緊給她打針,錢也花了不少,可是已經太遲了。這孩子也就是給過上的,可不能再耽擱了,今天早上為了想籌一點錢,就跑了一早上。﹂說到這裏,他嘆了口冷氣,又道:﹁真想不到落到今天這個日子!﹂
其實他投機失敗,一半也是迷信幫夫運的緣故。雖然他向不承認他的發跡是沾了曼璐的光,他心底裏對於那句話卻一直有三分相信。剛巧在曼璐去世的時候,他接連有兩樁事情不順手,心裏便有些害怕。做投機本來是一種賭博,越是怕越是輸,所以終至一敗塗地。而他就更加篤信幫夫之說了。
周媽絞了一把熱手巾送上來,給鴻才擦臉,他心不在焉地接過來,只管拿著擦手,把一雙手擦了又擦。周媽走開了,半晌,他忽然迸出一句話來:﹁我現在想想,真對不起她。﹂他背過身去望著曼璐的照片,便把那毛巾撳在臉上擤鼻子。他分明是在那裏流淚。
陽光正照在曼璐的遺像上,鏡框上的玻璃反射出一片白光,底下的照片一點也看不見,只看見那玻璃上的一層浮塵。曼楨呆呆地望著那照片,她姊姊是死了,她自己這幾年來也心灰意冷,過去那一重重糾結不開的恩怨,似乎都化為煙塵了。
鴻才又道:﹁想想真對不起她。那時候病得那樣,我還給她氣受,要不然她還許不會死呢。二妹,從前的事都是我不好,你不要恨你姊姊了。﹂他這樣自怨自艾,其實還是因為心疼錢的緣故,曼楨沒想到這一點,見他這樣引咎自責,便覺得他這人倒還不是完全沒有良心。她究竟涉世未深,她不知道往往越是殘暴的人越是怯懦,越是在得意的時候橫行不法的人,越是禁不起一點挫折,立刻就矮了一截子,露出一副可憐的臉相。她對鴻才竟於憎恨中生出一絲憐憫,雖然還是不打算理他,卻也不願意使他過於難堪。
鴻才向她臉上看了一眼,囁嚅著說道:﹁二妹,你不看別的,看這小孩可憐,你在這兒照應他幾天,等他好了再回去。我到朋友家去住幾天。﹂他唯恐她要拒絕似的,沒等說完就走出房去,從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來,向張媽手裏一塞,道:﹁你待會交給二小姐,醫生來了請她給付付。﹂又道:﹁我不是在王家就是在嚴先生那裏,萬一有什麼事,打電話找我好了。﹂說罷,馬上逃也似地匆匆走了。
曼楨倒相信他這次大概說話算話,說不回來就不回來。曼璐從前曾經一再地向她說,鴻才對她始終是非常敬愛,他總認為她是和任何女人都兩樣的,他只是一時神志不清做下犯罪的事情,也是因為愛得她太厲害的緣故。像這一類的話,在一個女人聽來是很容易相信的,恐怕沒有一個女人是例外。曼楨當時聽了雖然沒有什麼反應,曼璐這些話終究並不是白說的。
那天晚上她住在祝家沒回去,守著孩子一夜也沒睡。第二天早上她不能不照常去辦公,下班後又回到祝家來,知道鴻才已經來過一次又走了。曼楨這時候便覺得心定了許多,至少她可以安心看護孩子的病,不必顧慮到鴻才了。她本來預備再請豫瑾來一趟,但是她忽然想起來,豫瑾這兩天一定也很忙,不是說他太太昨天就要進醫院了嗎,總在這兩天就要動手術了。昨天她是急糊塗了,竟把這樁事情忘得乾乾淨淨。其實也可以不必再找豫瑾了,就找原來的醫生繼續看下去吧。
豫瑾對那孩子的病,卻有一種責任感,那一天晚上,他又到曼楨的寓所裏去過一趟,想問問她那孩子可好些了。二房東告訴他:曼楨一直沒有回來。豫瑾也知道他們另外有醫生在那裏診治著,既然有曼楨在那裏主持一切,想必決不會有什麼差池的,就也把這樁事情拋開了。
豫瑾在他丈人家寄居,他們的樓窗正對著曼楨的窗子,豫瑾常常不免要向那邊看一眼。這樣炎熱的天氣,那兩扇窗戶始終緊閉著,想必總是沒有人在家。隔著玻璃窗,可以看見裏面曬著兩條毛巾,一條粉紅色的搭在椅背上,一條白色的曬在繩子上,永遠是這個位置。那黃烘烘的太陽從早曬到晚,兩條毛巾一定要曬餿了。一連十幾天曬下來,毛巾烤成僵硬的兩片,顏色也淡了許多。曼楨一直住在祝家沒有回來,豫瑾倒也並不覺得奇怪,想著她姊姊死了,丟下這樣一個孩子沒人照應,他父親也許是一個沒有知識的人,也許他終日為衣食奔走,分不開身來,曼楨向來是最熱心的,最肯負責的,孩子病了,她當然義不容辭地要去代為照料。
但是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,豫瑾的太太施手術產下一個女孩之後,在醫院裏休養了一個時期,夫婦倆已經預備動身回六安去了,曼楨卻還沒有回來。豫瑾本來想到她姊夫家裏去一趟,去和她道別,但是究竟是不大熟悉的人家,冒冒失失地跑去似乎不大好,因此一直拖延著,也沒有去。
這一天,他忽然在無意中看見曼楨那邊開著一扇窗戶,兩條毛巾也換了一個位置,彷彿新洗過,又晾上了。他想著她一定是回來了。他馬上走下樓去,到對門去找她。
他來過兩次,那二房東已經認識他了,便不加阻止,讓他自己走上樓去。曼楨正在那裏掃地擦桌子,她這些日子沒回家,灰塵積得厚厚的。豫瑾帶笑在那開著的房門上敲了兩下,曼楨一抬頭看見是他,在最初的一剎那間她臉上似乎有一層陰影掠過,她好像不願意他來似的,但是豫瑾認為這大概是他的一種錯覺。
他走進去笑道:﹁好久不看見了。那小孩好了沒有?﹂曼楨笑道:﹁好了。我也沒來給你道喜,你太太現在已經出院了吧?是一個男孩子還是女孩子?﹂豫瑾笑道:﹁是個女孩子。蓉珍已經出來一個禮拜了,我們明天就打算回去了。﹂曼楨噯呀了一聲道:﹁就要走啦?﹂她拿抹布在椅子上擦了一把,讓豫瑾坐下。豫瑾坐下來笑道:﹁明天就要走了,下次又不知什麼時候才見得著,所以我今天無論如何要來看看你,跟你多談談。﹂他一定要在動身前再和她見一次面,也是因為她上次曾經表示過,她有許多話要告訴他,聽她的口氣彷彿有什麼隱痛似的。但是這時候曼楨倒又懊悔她對他說過那樣的話。她現在已經決定要嫁給鴻才了,從前那些事當然也不必提了。
桌上已經擦得很乾淨了,她又還拿抹布在桌上無意識地揩來揩去。揩了半天,又去伏在窗口抖掉抹布上的灰。本來是一條破舊的粉紅色包頭紗巾,她拿它做了抹布。兩隻手拎著它在窗外抖灰,那紅紗在夕陽與微風中懶洋洋地飄著。下午的天氣非常好。
豫瑾等候了一會,不見她開口,便笑道:﹁你上次不是說有好些事要告訴我麼?﹂曼楨道:﹁是的,不過我後來想想,又不想再提起那些事了。﹂豫瑾以為她是怕提起來徒然引起傷感,他頓了一頓,方道:﹁說說也許心裏還痛快些。﹂曼楨依舊不作聲。豫瑾沉默了一會,又道:﹁我這次來,是覺得你興致不大好,跟從前很兩樣了。﹂他雖然說得這樣輕描淡寫,說這話的時候卻是帶著一種感慨的口吻。
曼楨不覺打了個寒噤。他一看見她就看得出來她是疊經刺激,整個的人已經破碎不堪了?她一向以為她至少外貌還算鎮靜。她望著豫瑾微笑著說道:﹁你覺得我完全變了個人吧?﹂豫瑾遲疑了一下,方道:﹁外貌並沒有改變,不過我總覺得……﹂從前他總認為她是最有朝氣的,她的個性也有它的沉毅的一面,一門老幼都倚賴著她生活,她好像還餘勇可賈似的,保留著一種閑靜的風度。這次見面,她卻是那樣神情蕭索,而且有點恍恍惚惚的。僅僅是生活的壓迫決不會使她變得這樣厲害。他相信那還是因為沈世鈞的緣故。中間不知道出了些什麼變故,使他們不能有始有終。她既然不願意說,豫瑾當然也不便去問她。
他只能懇切地對她說:﹁我又不在此地,你明天常常給我寫信好不好?說老實話,我看你現在這樣,我倒是真有點不放心。﹂他越是這樣關切,曼楨倒反而一陣心酸,再也止不住自己,頓時淚如雨下。豫瑾望著她,倒呆住了,半晌,方才微笑道:﹁都是我不好,不要說這些了。﹂曼楨忽然衝口而出地說:﹁不,我是要告訴你︱︱﹂說到這裏,又噎住了。
她實在不知道從何說起。看見豫瑾那樣凝神聽著,她忽然腦筋裏一陣混亂,便又衝口而出地說道:﹁你看見的那個孩子不是姊姊的︱︱﹂豫瑾愕然望著她,她把臉別了過去,臉上卻是一種冷淡而強硬的神情。豫瑾想道:﹁那孩子難道是她的麼,是她的私生子,交給她姊姊撫養的?是沈世鈞的孩子?還是別人的︱︱世鈞離開她就是為這個原因?﹂一連串的推想,都是使他無法相信的,都在這一剎那間在他腦子裏掠過。
曼楨卻又斷斷續續地說起話來了,這次她是從豫瑾到她家裏來送喜柬的那一天說起,就是那一天,她陪著她母親到她姊姊家去探病。在敘述中間,她總想為她姊姊留一點餘地,因為豫瑾過去和曼璐的關係那樣深,他對曼璐的那點殘餘的感情她不願意加以破壞。況且她姊姊現在已經死了。但是她無論怎麼樣為曼璐開脫,她被禁閉在祝家一年之久,曼璐始終坐視不救,這總是實情。豫瑾簡直覺得駭然。他不能夠想像曼璐怎樣能夠參與這樣卑鄙的陰謀。曼璐的丈夫他根本不認識,可能是一個無惡不作的人,但是曼璐︱︱他想起他們十五六歲的時候剛見面的情景,還有他們初訂婚的時候,還有後來,她為了家庭出去做舞女,和他訣別的時候。他所知道的她是那樣一個純良的人。就連他最後一次看見她,他覺得她好像變粗俗了,但那並不是她的過錯,他相信她的本質還是好的。怎麼她對她自己的妹妹竟是這樣沒有人心。
曼楨繼續說下去,說到她生產後好容易逃了出來,她母親輾轉訪到她的下落,卻又勸她回到祝家去。豫瑾覺得她母親簡直荒謬到極點,他氣得也說不出話來。曼楨又說到她姊姊後來病重的時候親自去求她,叫她為孩子的緣故嫁給鴻才,又被她拒絕了。她說到這裏,聲調不由得就變得澀滯而低沉,因為當時雖然拒絕了,現在也還是要照死者的願望做去了。她也曉得這樣做是不對的,心裏萬分矛盾,非常需要跟豫瑾商量商量,但是她實在沒有勇氣說出來。她自己心裏覺得非常抱愧,尤其覺得愧對豫瑾。
剛才她因為顧全豫瑾的感情,所以極力減輕她姊姊應負的責任,無形中就加重了鴻才的罪名,更把他表現成一個惡魔,這時候她忽然翻過來說要嫁給他,當然更無法啟齒了。其實她也知道,即使把他說得好些,成為一個多少是被動的人物,豫瑾也還是不會贊成的。這種將錯就錯的婚姻,大概凡是真心為她打算的朋友都不會贊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