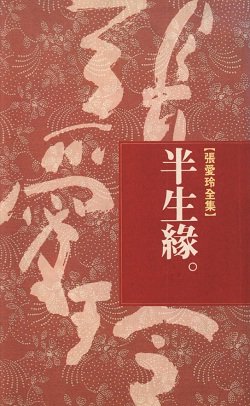叔惠把兩隻手插在褲袋裏,露出他裏面穿的絨線背心,灰色絨線上面滿綴著雪珠似的白點子。他母親便問道:﹁你這背心是新的?是機器織的還是打的?﹂叔惠道:﹁是打的。﹂許太太道:﹁哦?是誰給你打的?﹂叔惠道:﹁顧小姐,你不認識的。﹂許太太道:﹁我知道的︱︱不就是你那個同事的顧小姐嗎?﹂
曼楨本來跟世鈞說要給他打件背心,但是她這種地方向來是非常周到的,她替叔惠也織了一件。她的絨線衫口袋裏老是揣著一團絨線,到小飯館子裏吃飯的時候也手不停揮地打著。是叔惠的一件先打好,他先穿出來了。被他母親看在眼裏,他母親對於兒子的事情也許因為過分關心的緣故,稍微有點神經過敏,從此倒添了一樁心事。當時她先擱在心裏沒說什麼。叔惠是行蹤無定的,做母親的要想釘住他跟他說兩句心腹話,簡直不可能。倒是世鈞,許太太和他很說得來。她存心要找個機會和他談談,從他那裏打聽打聽叔惠的近況,因為兒女到了一定年齡,做父母的跟他們簡直隔閡得厲害,反而朋友接近得多。
第二天是一個星期日,叔惠出去了,他父親也去看朋友去了。郵差送了封信來,許太太一看,是世鈞家裏寄來的,便送到他房間裏來。世鈞當著她就把信拆開來看,她便倚在門框上,看著他看信,問道:﹁是南京來的吧?你們老太太好呀?﹂世鈞點點頭,道:﹁她說要到上海來玩一趟。﹂許太太笑道:﹁你們老太太興致這樣好!﹂世鈞皺著眉笑道:﹁我想她還是因為我一直沒回去過,所以不放心,想到上海來看看。其實我是要回去一趟的。我想寫信去告訴她,她也可以不必來了︱︱她出一趟門,是費了大事的,而且住旅館也住不慣。﹂許太太歎道:﹁也難怪她惦記著,她現在就你這麼一個孩子嘛!你一個人在上海,也不怪她不放心︱︱她倒沒催你早一點結婚麼?﹂世鈞頓了一頓,微笑道:﹁我母親這一點倒很開通。也是因為自己吃了舊式婚姻的苦,所以對於我她並不干涉。﹂許太太點頭道:﹁這是對的。現在這世界,做父母的要干涉也不行呀!別說像你們老太太跟你,一個在南京,一個在上海,就像我跟叔惠這樣住在一幢房子裏,又有什麼用?他外邊有女朋友,他哪兒肯對我們說?﹂世鈞笑道:﹁那他要是真的有了結婚的對象,他決不會不說的。﹂許太太微笑不語,過了一會,便又說道:﹁你們同事有個顧小姐,是怎麼一個人?﹂世鈞倒愣了一愣,不知道為什麼馬上紅了臉,道:﹁顧曼楨呀?她人挺好的,可是︱︱她跟叔惠不過是普通朋友。﹂許太太半信半疑地哦了一聲,心想,至少那位小姐對叔惠很不錯,要不怎麼會替他打絨線背心。除非她是相貌長得醜,所以叔惠對她並沒有意思。因又笑道:﹁她長得難看是吧?﹂世鈞不由得笑了一笑,道:﹁不,她……並不難看。不過我確實知道她跟叔惠不過是普通朋友。﹂他自己也覺得他結尾這句話非常無力,一點也不能保證叔惠和曼楨結合的可能。許太太要疑心也還是要疑心的。只好隨她去吧。
世鈞寫了封信給他母親,答應說他不久就回來一趟。他母親很高興,又寫信來叫他請叔惠一同來。世鈞知道他母親一定是因為他一直住在叔惠家裏,她要想看看他這個朋友是個什麼樣的人,是否對於他有不良的影響。他問叔惠可高興到南京去玩一趟。這一年的雙十節恰巧是一個星期五,和週末連在一起,一共放三天假。他們決定趁這個機會去痛痛快快玩兩天。
在動身的前夕,已經吃過晚飯了,叔惠又穿上大衣往外跑。許太太知道他剛才有一個女朋友打電話來,便道:﹁這麼晚了還要出去,明天還得起個大早趕火車呢!﹂叔惠道:﹁我馬上回來的。一個朋友有兩樣東西託我帶到南京去。我去拿一拿。﹂許太太道:﹁喲,東西有多大呀,裝得下裝不下?你的箱子我倒已經給你理好了。﹂她還在那裏念叨著,叔惠早已走得無影無蹤了。
他才去了沒有一會,倒又回來了,走到樓梯底下就往上喊:﹁喂,有客來了!﹂原來是曼楨來了,他在衖堂口碰見她,便又陪著她一同進來。曼楨笑道:﹁你不是要出去麼?你去吧,真的,沒關係的。我沒有什麼事情︱︱我給你們帶了點點心來,可以在路上吃。﹂叔惠道:﹁你幹嘛還要買東西?﹂他領著她一同上樓,樓梯上有別的房客在牆上釘的晾衣裳繩子,晾滿了一方一方的尿布,一根繩子斜斜地一路牽到樓上去。樓梯口又是煤球爐子,又是空肥皂箱、洋油桶;上海人家一幢房子裏住上幾家人家,常常就成為這樣一個立體化的大雜院。叔惠平常走出去,西裝穿得那麼挺括,人家大約想不到他家裏是這樣一個情形。他自己也在那裏想著:這是曼楨,還不要緊,換了一個比較小姐脾氣的女朋友,可不能把人家往家裏帶。
走到三層樓的房門口,他臉上做出一種幽默的笑容,向裏面虛虛地一伸手,笑道:﹁請請請。﹂由房門裏望進去,迎面的牆上掛著幾張字畫和一隻火腿。叔惠的父親正在燈下洗碗筷。他在正中的一張方桌上放著一隻臉盆,在臉盆裏晃蕩晃蕩洗著碗。今天是他洗碗,因為他太太吃了飯就在那裏忙著絮棉襖︱︱他們還有兩個孩子在北方念書,北方的天氣冷得早,把他們的棉袍子給做起來,就得給他們寄去了。
許太太看見來了客,一聽見說是顧小姐,知道就是那個絨線背心的製作者,心裏不知怎麼卻有點慌張,笑嘻嘻地站起來讓坐,嘴裏只管嘰咕著:﹁看我這個樣子!弄了一身的棉花!﹂只顧忙著拍她衣服上粘的棉花衣子。許裕舫在家裏穿著一件古銅色對襟裌襖,他平常雖然是那樣滿不在乎,來了這麼個年輕的女人,卻使他侷促萬分,連忙加上了一件長衫。這時候世鈞也過來了。許太太笑道:﹁顧小姐吃過飯沒有?﹂曼楨笑道:﹁吃過了。﹂叔惠陪著坐了一會,曼楨又催他走,他也就走了。
裕舫在旁邊一直也沒說話,到現在方才開口問他太太:﹁叔惠上哪兒去了?﹂他太太雖然知道叔惠是到女朋友家去了,她當時就留了個神,很圓滑地答道:﹁不知道,我只聽見他說馬上就要回來的,顧小姐你多坐一會。這兒實在亂得厲害,要不,上那邊屋裏坐坐吧。﹂她把客人讓到叔惠和世鈞的房間裏去,讓世鈞陪著,自己就走開了。
許太太把她剛才給曼楨泡的一杯茶也送過來了。世鈞拿起熱水瓶來給添上點開水,又把檯燈開了。曼楨看見桌上有個鬧鐘,便拿過來問道:﹁你們明天早上幾點鐘上火車?﹂世鈞道:﹁是七點鐘的車。﹂曼楨道:﹁把鬧鐘撥到五點鐘,差不多吧?﹂她開著鐘,那軋軋軋的聲浪,反而顯出這間房間裏面的寂靜。
世鈞笑道:﹁我沒想你今天會來。……為什麼還要買了點心來呢?﹂曼楨笑道:﹁咦,你不是說,早上害許伯母天不亮起來給你們煮稀飯,你覺得不過意,我想著明天你們上火車,更要早了,你一定不肯麻煩人家,結果一定是餓著肚子上車站,所以我帶了點吃的來。﹂
她說這個話,不能讓許太太他們聽見,聲音自然很低。世鈞走過來聽,她坐在那裏,他站得很近,在那一剎那間,他好像是立在一個美麗的深潭的邊緣上,有一點心悸,同時心裏又感到一陣陣的蕩漾。她的話早說完了,他還沒有走開。也許不過是頃刻間的事,但是他自己已經覺得他逗留得太久了,她一定也有同感,因為在燈光下可以看見她臉上有點紅暈。她亟於要打破這一個局面,便說:﹁你忘了把熱水瓶蓋上了。﹂世鈞回過頭去一看,果然那熱水瓶像煙囪似的直冒熱氣,剛才倒過開水就忘了蓋上,今天也不知道怎麼這樣心神恍惚。他笑著走過去把它蓋上了。
曼楨道:﹁你的箱子理好了沒有?﹂世鈞笑道:﹁我也不帶多少東西。﹂他有一隻皮箱放在床上,曼楨走過去,扶起箱子蓋來看看,裏面亂七八糟的。她便笑道:﹁我來給你理一理。不要讓你家裏人說你連箱子都不會理,更不放心讓你一個人在外面了。﹂世鈞當時就想著,她替他理箱子,恐怕不大妥當,讓人家看見了要說閒話的。然而他也想不出適當的話來攔阻她,曼楨有些地方很奇怪,羞澀起來很羞澀,天真起來又很天真︱︱而她並不是一個一味天真的人,也並不是一個一味怕羞的人。她這種矛盾的地方,實在是很費解。
曼楨見他呆呆地半天不說話,便道:﹁你在那裏想什麼?﹂世鈞笑了一笑,道:﹁唔?︱︱﹂他回答不出,看見她正在那裏摺疊一件襯衫,便隨口說道:﹁等我回來的時候,我那件背心大概可以打好了吧?﹂曼楨笑道:﹁你禮拜一準可以回來麼?﹂世鈞笑道:﹁禮拜一一定回來。沒有什麼必要的事情,我不想請假。﹂曼楨道:﹁你這麼些時候沒回去過,你家人一定要留你多住幾天的。﹂世鈞笑道:﹁不會的。﹂
那箱子蓋忽然自動地扣下來,正斫在曼楨的手背上。才扶起來沒有一會,又扣了下來。世鈞便去替她扶著箱子蓋。他坐在旁邊,看著他的襯衫領帶和襪子一樣一樣經過她的手,他有一種異樣的感覺。
許太太裝了兩碟子糖果送了來,笑道:﹁顧小姐吃糖。︱︱呦,你替世鈞理箱子呀?﹂世鈞注意到許太太已經換上了一件乾淨衣服,臉上好像還撲了點粉,那樣子彷彿是預備到這兒來陪客人談談似的,然而她結果並沒有坐下,敷衍了兩句就又走了。
曼楨道:﹁你的雨衣不帶去?﹂世鈞道:﹁我想不帶了︱︱不見得剛巧碰見下雨,一共去這麼兩天工夫。﹂曼楨道:﹁你禮拜一一定回來麼?﹂話已經說出口,她才想起來剛才已經說過了,自己也笑了起來。就在這一陣笑聲中匆匆關上箱子,拿起皮包,說:﹁我走了。﹂世鈞看她那樣子好像相當窘,也不便怎麼留她,只說了一聲:﹁還早呢,不再坐一會兒?﹂曼楨笑道:﹁不,你早點睡吧。我走了。﹂世鈞笑道:﹁你不等叔惠回來了?﹂曼楨笑道:﹁不等了。﹂
世鈞送她下樓,她經過許太太的房間,又在門口向許太太夫婦告辭過了,許太太送她到大門口,再三叫她有空來玩。關上大門,許太太便和世鈞說:﹁這顧小姐真好,長得也好!﹂她對他稱讚曼楨,彷彿對於他們的關係有了一種新的認識似的,世鈞倒覺得有點窘,他只是唯唯諾諾,沒說什麼。
回到房間裏來,他的原意是預備早早的上床睡覺;要鋪床,先得把床上那隻箱子拿掉,但是他結果是在床沿上坐下來了,把箱子開開來看看,又關上了,心裏沒著沒落的,非常無聊。終於又站起來,把箱子鎖上了,從床上拎到地下。鑰匙放到口袋裏去,手指觸到袋裏的一包香煙,順手就掏出來,抽出一根來點上。既然點上了,總得把這一根抽完了再睡覺。
看看鐘,倒已經快十一點了。叔惠還不回來。夜深人靜,可以聽見叔惠的母親在她房裏軋軋軋轉動著她的手搖縫衣機器。大概她在等著替叔惠開門,不然她這時候也已經睡了。
世鈞把一支香煙抽完了,有點口乾,去倒杯開水喝。他的手接觸到熱水瓶的蓋子,那金屬的蓋子卻是滾燙的。他倒嚇了一跳,原來裏面一隻軟木塞沒有塞上,所以熱氣不停地冒出來,把那蓋子熏得那麼燙。裏面的水已經涼了。他今天也不知怎麼那樣糊塗,這隻熱水瓶,先是忘了蓋;蓋上了,又忘了把裏面的軟木塞塞上。曼楨也許當時就注意到了,但是已經提醒過他一次,不好意思再說了。世鈞想到這裏,他儘管一方面喝著涼開水,臉上卻熱辣辣起來了。
樓窗外有人在吹口哨,一定是叔惠。叔惠有時候喜歡以吹口哨代替敲門,因為晚上天氣冷,他兩手插在大衣袋裏,懶得拿出來。世鈞心裏想,許太太在那裏軋軋軋做著縫衣機器,或者會聽不見;他既然還沒有睡,不妨下去一趟,開一開門。
他走出去,經過許太太房門口,卻聽見許太太在那裏說話,語聲雖然很低,但是無論什麼人,只要一聽見自己的名字,總有點觸耳驚心,決沒有不聽見的道理。許太太在那兒帶笑帶說:﹁真想不到,世鈞這樣不聲不響的一個老實頭兒,倒把叔惠的女朋友給搶了去了!﹂裕舫他是不會竊竊私語的,向來是聲如洪鐘。他說道:﹁叔惠那小子︱︱就是一張嘴!他哪兒配得上人家!﹂這位老先生和曼楨不過匆匆一面,對她的印象倒非常之好。這倒沒什麼,但是他對自己的兒子評價過低,卻使他太太感到不快。她沒有接口,軋軋軋又做起縫衣機器來。世鈞就藉著這機器的響聲作為掩護,三級樓梯一跨,跑回自己房來。
許太太剛才說的話,他現在才回過味來。許太太完全曲解了他們三個人之間的關係,然而他聽到她的話,除了覺得一百個不對勁以外,紊亂的心緒裏卻還夾雜著一絲喜悅,所以心裏也說不上來是一種什麼滋味。
叔惠還在樓窗口外吹著口哨,並且蓬蓬蓬敲著門了。
第四章
他們乘早班火車到南京。從下關車站到世鈞家裏有公共汽車可乘,到家才只有下午兩點鐘模樣。
世鈞每一次回家來,一走進門,總有點詫異的感覺,覺得這地方比他記憶中的家要狹小得多,大約因為他腦子裏保留的印象還是幼年時代的印象,那時候他自己身個兒小,從他的眼睛裏看出來,當然一切都特別放大了一圈。
他家裏開著一爿皮貨店,自己就住在店堂樓上。沈家現在闊了,本來不靠著這爿皮貨店的收入,但是家裏省儉慣了,這些年來一直住在這店堂樓上,從來不想到遷移。店堂裏面陰暗而寬敞,地下鋪著石青的方磚。店堂深處停著一輛包車,又放著一張方桌和兩把椅子,那是給店裏的帳房和兩個年份多些的夥計在那裏起坐和招待客人的。桌上擱著茶壺茶杯,又有兩隻瓜皮小帽覆在桌面上,看上去有一種閒適之感。抬頭一看,頭上開著天窗,屋頂非常高,是兩層房子打通了的。四面圍著一個走馬樓,樓窗一扇扇都是寶藍彩花玻璃的。
世鈞的母親一定是在臨街的窗口瞭望著,黃包車拉到門口,她就看見了。他這裏一走進門,他母親便從走馬樓上往下面哇啦一喊:﹁阿根,二少爺回來了!幫著拿拿箱子!﹂阿根是包車伕,他隨即出現了,把他們手裏的行李接過去。世鈞便領著叔惠一同上樓。沈太太笑嘻嘻迎出來,問長問短,叫女傭打水來洗臉,飯菜早預備好了,馬上熱騰騰地端了上來。沈太太稱叔惠為﹁許家少爺﹂。叔惠人既漂亮,一張嘴又會說,老太太們見了自然是喜歡的。
世鈞的嫂嫂也帶著孩子出來相見。一年不見,他嫂嫂又蒼老了許多。前一向聽見說她有腰子病,世鈞問她近來身體可好,他嫂嫂說還好。他母親說:﹁大少奶奶這一向倒胖了。倒是小健,老是不舒服,這兩天出疹子剛好。﹂他這個侄兒身體一直單弱,取名叫小健,正是因為他不夠健康的緣故。他見了世鈞有點認生,大少奶奶看他彷彿要哭似的,忙道:﹁不要哭,哭了奶奶要發脾氣的!﹂沈太太笑道:﹁奶奶發起脾氣來是什麼樣子?﹂小健便做出一種嗚嗚的聲音,像狗的怒吼。沈太太又道:﹁媽發起脾氣來是什麼樣?﹂他又做出那嗚嗚的吼聲。大家都笑了。世鈞心裏想著,家裏現在就只有母親和嫂嫂兩個人,帶著這麼一個孩子過活著,哥哥已經死了,父親又不大回家來︱︱等於兩代寡居,也夠淒涼的,還就靠這孩子給這一份人家添上一點生趣。
小健在人前只出現了幾分鐘,沈太太便問叔惠,﹁許家少爺你出過疹子沒有?﹂叔惠道:﹁出過了。﹂沈太太道:﹁我們世鈞也出過了,不過還是小心點的好。小健雖然已經好了,仍舊會過人的。奶媽你還是把他帶走吧。﹂
沈太太坐在一邊看著兒子吃飯,問他們平常幾點鐘上班,幾點鐘下班,吃飯怎麼樣,日常生活情形一一都問到了。又問起冬天屋子裏有沒有火,苦苦勸世鈞做一件皮袍子穿,馬上取出各種細毛的皮統子來給他挑揀。揀過了,仍舊收起來,叫大少奶奶幫著收到箱子裏去。大少奶奶便說:﹁這種洋灰鼠的倒正好給小健做個皮斗篷。﹂沈太太道:﹁小孩子不可以給他穿皮的︱︱火氣太大了。我們家的規矩向來這樣,像世鈞他們小時候,連絲棉的都不給他們穿。﹂大少奶奶聽了,心裏很不高興。
沈太太因為兒子難得回來一次,她今天也許興奮過度了,有點神情恍惚,看見傭人也笑嘻嘻的,一會兒說﹁快去這樣﹂,一會兒說﹁快去那樣﹂,顛三倒四,跑出跑進地亂發號令,倒好像沒用慣傭人似的,不知道要怎樣鋪張才好,把人支使得團團轉。大少奶奶在旁邊要幫忙也插不上手去。世鈞看見她母親這樣子,他不知道這都是因為他的緣故,他只是有一點傷感,覺得他母親漸漸露出老態了。
世鈞和叔惠商量著今天先玩哪幾個地方,沈太太道:﹁找翠芝一塊兒去吧,翠芝這兩天也放假。﹂翠芝是大少奶奶的表妹,姓石。世鈞馬上就說:﹁不要了,今天我還得陪叔惠到一個地方去,有人託他帶了兩樣東西到南京來,得給人家送去。﹂被他這樣一擋,沈太太就也沒說什麼了,只叮囑他們務必要早點回來,等他們吃飯。
叔惠開箱子取出那兩樣託帶的東西,沈太太又找出紙張和繩子來,替他重新包紮了一下。世鈞在旁邊等著,他立在窗前,正看見他侄兒在走馬樓對面,伏在窗口向他招手叫二叔。看到小健,非常使他想起自己的童年。因而就聯想到石翠芝。翠芝和他是從小就認識的,雖然並不是什麼青梅竹馬的小情侶,他倒很記得她的。倒是快樂的回憶容易感到模糊,而刺心的事情︱︱尤其是小時候覺得刺心的事情︱︱是永遠記得的,常常無緣無故地就浮上心頭。
他現在就又想起翠芝的種種。他和翠芝第一次見面,是在他哥哥結婚的時候。他哥哥結婚,叫他做那個捧戒指的僮兒,在那婚禮的行列裏他走在最前面。替新娘子拉紗的有兩個小女孩,翠芝就是其中的一個。在演習儀式的時候,翠芝的母親在場督導,總是挑眼,嫌世鈞走得太快了。世鈞的母親看見翠芝,卻把她當寶貝,趕著她兒呀肉的叫著,想要認她做乾女兒。世鈞不知道這是一種社交上的策略,小孩子家懂得什麼,看見他母親這樣疼愛這小女孩,不免有些妒忌。他母親叫他帶著她玩,說他比她大得多,應當讓著她,不可以欺負她。世鈞教她下象棋。她那時候才七歲,教她下棋,她只是椅子上爬上爬下的,心不在焉。一會兒又趴在桌上,兩支胳膊肘子撐在棋盤上,兩手托著腮,把一雙漆黑的眼睛灼灼地凝視著他,忽然說道:﹁我媽說你爸爸是個暴發戶。噯!﹂世鈞稍微愣了一愣,就又繼續移動著棋子:﹁我吃你的馬。哪,你就拿炮打我︱︱﹂翠芝又道:﹁我媽說你爺爺是個毛毛匠。﹂世鈞道:﹁吃你的象。喏,你可以出車了。︱︱打你的將軍!﹂
那一天後來他回到家裏,就問他母親:﹁媽,爺爺從前是幹什麼的?﹂他母親道:﹁爺爺是開皮貨店的。這爿店不就是他開的麼?﹂世鈞半天不作聲,又道:﹁媽,爺爺做過毛毛匠嗎?﹂他母親向他看了一眼,道:﹁爺爺從前沒開店的時候本來是個手藝人,這也不是什麼難為情的事情,也不怕人家說的。﹂然而她忽然又厲聲問道:﹁你聽見誰說的?﹂世鈞沒告訴她。她雖然說這不是什麼難為情的事,她這種神情和聲口已經使他深深地感到羞恥了。但是更可恥的是他母親對翠芝母女那種巴結的神氣。
世鈞的哥哥結婚那一天,去拍結婚照,拉紗的和捧戒指的小孩預先都經各人的母親關照過了,鎂光燈一亮的時候,要小心不要閉上眼睛。後來世鈞看到那張結婚照片,翠芝的眼睛是緊緊閉著的。他覺得非常快心。
那兩年他不知道為什麼,簡直沒有長高,好像完全停頓了。大人常常嘲笑他:﹁怎麼,你一定是在屋子裏打著傘來著?﹂因為有這樣一種禁忌,小孩子在房間裏打著傘,從此就不再長高了。翠芝也笑他矮,說:﹁你比我大,怎麼跟我差不多高?還是個男人。︱︱將來長大一定是個矮子。﹂幾年以後再見面,他已經比她高出一個頭半了,翠芝卻又說:﹁怎麼你這樣瘦?簡直瘦得像個螞蚱。﹂這大約也是聽見她母親在背後說的。